


从山村到燕园
(一)出自幽谷
我生于1964年,老家在重庆市酉阳县。酉阳当时隶属四川省涪陵地区,全县地处于武陵山区腹地,酉水河从县境南部流过,而乌江流入重庆市的地方,就是酉阳县的西北部。我家到我这一代,定居酉阳县已将近三百年,可以称得上地道的土著。我家所在的小山村在与湖北省交界处,远离县城,不通公路。
1971年春,我开始上学。从家里到学校要翻两个小山头。三年级时到公社所在地的小学就读,要翻三个小山头。小学五年读完后,全班没有地方上中学,于是小学的这个班改成初中,两年之后,又变成高中班。我在这所小学上了六年学,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1978年时读到了高中一年级。
在这样的山村小学读书,知识水平当然不值一提。高一暑假之前,县里举行了一次考试,成绩好的可以去县一中或二中读高二。记得有一道数学题是,(a-b)的平方在什么条件下大于零。我能读懂题,但完全不会答。可能因为我的语文还过得去,我竟然被县一中录取了。县一中总共只招了三个班计约100人,我所在的文科班只有三十多人,录取率估计不到百分之一,我实在是太幸运了!是这次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酉阳县一中不在县城,在县城的是二中,估计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少见。原因是一中成立得早,曾是四川省立第五中学,长期都是附近几个县最好的中学。1978年秋季开学时,老师说,只要你们认真读,让你们考上大学,这点水平老师还是有的。老师又说,第一个学期,我们按成绩最差的同学的水平教,下个学期,我们按成绩最好的同学的水平教。
老师真的就是这么教的,所以在高二这一个学年里,老师一直在照顾我:第一个学期是因为我的成绩最差,第二个学期是因为我的成绩最好。第一个学期开学时,我只认得六个英语字母,又不认识拼音,所以打算不学英语。老师对我说,还是学吧,说不定以后能考个好大学呢。老先生送了我几个英语练习本,要我每晚去他家,由他单独给我补英语课。我一个农家孩子,能遇到这样的老师,真是太有福气了!我高考的英语成绩有五十几分,据说是全县第一。
高考前几天,老师说,这几天大家都出去玩,可以爬爬山什么的,但不准读书,教室上锁,图书馆也不许去。当时每个同学都只有一条被子,没有褥子,所以需要两人合睡一个被窝,和我睡同一个被窝的同学比我大两三岁,我们关系很好。我们俩都很听老师的话,那几天说不读书就不读书,整天爬山、游泳。这哥们儿本来知识水平高于我,但高考在我们班屈居第二,上了复旦,应该是因为没有我那么放松。
我能轻松地应考,要感谢家父。他老人家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,知道你学习很努力,不论考得如何,我都对你很满意。家父只读了六年私塾,但他的中文水平足以胜任在大学教授古文,他撰写的对联挂到北大去也不丢人。我在大三暑假时回家,同家父聊天时,说起自己刚读了《聊斋》里的《胭脂》,他随口就背诵了施愚山的判词。他一辈子种地,可能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,乡下人读书也没什么用,所以他自己没有教过我读书,但他总是给我信心,他常说,读书不难。
就这样,县一中只用了一年时间,就让我以384分的总成绩,成为恢复高考后酉阳考入北大的第一人。

(家在武陵山,自幼识饥寒。劬劳生我者,而今梦里看。我到北京上学后,父亲信中附寄的照片。我家合照只有此帧,里面恰好没有我。拍摄地点是祖居木屋前。我在乡下时也经常赤脚,刚到北京时脚上还有伤疤尚未愈合。右边的二弟于1988年考入四川大学,是我们公社的第二个大学生。如今二老都已去世,我兄妹五人也都已经人到中年。)
(二)观光上国
1979年8月下旬,我在湖北省咸丰县一位亲戚家作客。一天清晨,家父来接我回家。他一大早走了十几里山路,显然很兴奋,一见到我就拿出前一天下午收到的录取通知书,让我先睹为快。我却相当平静:此前已经知道自己过了录取分数线,以后不必跟着父亲种地了,对我而言,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所传达的信息,也只有这么多。
接下来几天是乡邻轮流请我吃饭,给我湊路费。印象最深的是咸丰县的一位族叔,派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一位堂兄,翻山越岭给我送来了一元钱。这样收到的资助,总计好像接近三十元。
村里没有人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北京,所以我8月31日就动身了。天刚亮的时候,家母送到村边,流着泪叮嘱了几句,由家父送我赶赴县城。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,再加上两个小时的汽车颠簸,父子俩于下午到达酉阳县城。
因为在县城没有熟人,买好第二天的车票后,父子俩便在街头闲逛。其间碰到了县招办主任,他是我所在考场的监考老师,我的班主任老师曾敦促过他,监考期间不要“吓唬”某两位考生,因为那是他的“得意门生”——其中一位是我,另一位是同我睡一个被窝的那位同学——没想到主任居然还能在街上认出我来。主任说,快写份申请来,给你补助点路费。我在街边写了几句,主任接过,不久就给我拿来三十元。后来看到“立等可得”的广告,每每想起这一件事。
9月1日,家父送我坐上汽车。车上有两位探亲后返回部队的士兵和一位去部队探亲的军嫂,家父请求他们一路照顾我。至于送到学校,那是谁都没有想过的事情:贫穷真的限制想像力!当日下午抵达龚滩镇。这是酉阳县的一个古镇,坐落在乌江岸边,现在已成旅游热点。我半夜时在龚滩上船,第二天傍晚到达涪陵。乌江在涪陵汇入长江,我在此换乘长江的班船。9月3日上午,船靠重庆朝天门码头。
朝天门码头当时就有帮人搬运行李的“棒棒”。我只有一件行李,是一口木箱子。高考时我还不满十五岁,体检的身高只有一米四五。记得爬朝天门的台阶很是吃力,行李好像是由棒棒帮忙搬的。同行的士兵和军嫂带着我买好火车票后,又游了解放碑,深夜时分登上重庆直达北京的特快。当时的线路需要从成都、宝鸡绕一大圈,火车到达北京站时,已是9月6日凌晨,我的双腿都坐肿了。
从北京站坐103到动物园,再换乘332到海淀,这一段行程是我独自完成的。我从小南门进入北大,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始接待新生,门卫看我是哲学系的学生,把我领到了38楼。几位七六级的师兄把我领到他们宿舍,带我去食堂吃饭,去澡堂洗澡(平生第一次,以前只在河里洗),凑了一身衣服给我换上。韩信所谓“解衣衣我,推食食我”,估计有所夸张,其实超不过我得到的待遇。
我这样一位师弟的出现,想必师兄们也颇感意外,当晚熄灯后,他们还议论了一阵,谈得最多的是,这种年龄的学生,学校不应该录取到哲学系。躺在师兄们给我安排的床上,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,不禁泪下如雨,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。或许是潜意识已经告诉我:此前的我已于此时死,而此时其实是我的又一次降生,降生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。此时的泪水,或许正是这个新生儿的哭喊,是他对旧我的怀念,对前路的恐惧?

(自行束修日,早充观国宾。燕园游四载,童子得成人。大一时与室友曹晓明师兄合影。晓明师兄为校足球队队员,待我情同手足。)
我的大学生活并不是多么快乐,好像一直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,还没等到适应的那一天,就毕业了。只有两件事,从中能够明显看出,在北大期间我的变化还是很大的。
一是身体的成长。我们班的一位大哥后来告诉我说,你上学时人很矮,但肚子大,长得像个小地主似的。那当然是多年营养不良的后果。到北大后,伙食大为改善。我毕业时身高长到了一米七八,平均每年长八厘米。那几年我特别能吃,上午到第四节课时,就觉得饥肠辘辘了。班上的师姐们给我粮票,北京的同学有时还邀我到家作客,那都是我改善生活的好机会。
二是我自学了英语。我在北大只听了一个学期的英语课,其中头一个月是由一位中年老师授课。他要求严格,批评我们的英语发音时,不留情面。感谢他让我知道了我的英语发音有多么差。后来我觉得自学的效率更高,就不去听英语课了。北大对学生上不上课管得不是特别严,我逃课较多。由于是自学英语,修满头两年必修的课程后,我并没有中断英语学习。在毕业前搞过一次全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比赛,参赛的人不少,我居然得了特等奖,据说是第五名。毕业时考本系的研究生,虽然落榜,但英语成绩考了80多分,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分数了。我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,但对自己英语一直比较自信。在接近五十岁时又自学德语,现可以读懂康德的原著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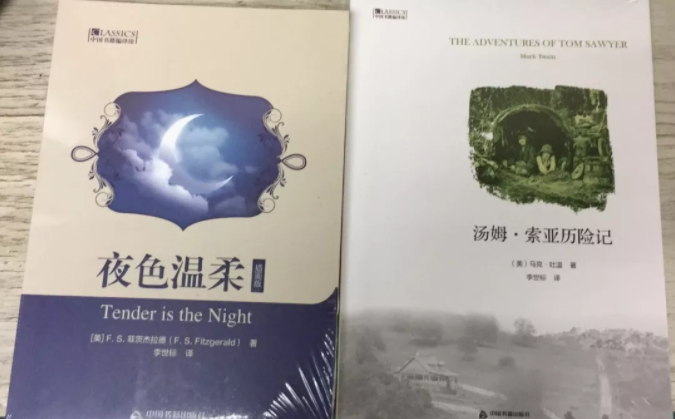
(清风吹木叶,微芒下稍头。曲径苍苔暗,照见绿莹浮。——我译的《夜色温柔》卷首所引济慈诗句。这是我近几年翻译的两本书。这两本书都有多个中译本,我相信这两本都经得起对照)
(三)知命乐天
离开北大的时候,我并没有感到多少失落。我分到武汉,两年后又调到深圳,如今依然混迹在深圳街头,事业上一事无成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我一直没有弄清楚,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。北大意味着出类拔萃,也就意味着出类拔萃的机会。假如明白得早一点,我此前的多次选择,都会不同。这些年我说过的几段话,颇能反映出我理解北大的过程。
2003年,我在毕业二十周年纪念册上写到:“心境的平和,行为的中庸,逻辑的极致,于我而言便是哲学,它帮助我度过了迷惘的四年,使我有了安身立命的支柱。感谢上苍让我与如许多位哲人为伍,祝愿大家平安喜乐。”
这说的是我的北大师友。他们中有学术大师,有成功的商人,有高级官员,有科学家也有艺术家;即令平常如我者,也自有一种气质,能够让人们看出北大的与众不同。我能与他们结缘,何其荣幸!
2016年在酉阳县一中120周年校庆致辞,我说:“我出身于贫苦农家,生长于穷乡僻壤,如果没有母校的教诲,我的世界就只是祖居所在的那一小片山沟,即使温饱可求,识见必难开悟,将如井蛙不可以语于海,夏虫不可以语于冰,精神上一定是贫困的。母校教我读书明理,使我一生免遭精神贫困之苦。我的这一段幸运,各位校友都经历过,相信大家都有同样深刻的感受。”
“使我们免于精神贫困,这是母校对我们莫大的恩德。母校使我们出自幽谷迁于乔木,更令我们变换气质脱胎换骨。母校把一块块顽石炼成了通灵宝玉,使其无论有无补天的机遇,却都有引领社会的才能,其见识之高远,则广弥六合,纵贯古今;其气度之宏毅,则置身于朝堂可以指点江山,辗转于市井可以笑傲江湖。诚如中山先生所言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布衣亦可笑王侯。母校为我们读万卷书指点了门径,是我们万里之行的起点和归宿,对我们恩德至深。”
这些话适用于我的中学母校,也完全适用于我的大学母校。陆九渊曾说:“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,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。”我没有这样的自信,但我现在知道,北大对我的教育,确能让我“堂堂的做个人”。
今年春天,我在老家接待了两位师弟,他们都是北京人。有一段行程只有我们三人,沿着与湖北交界处的河流跋涉了两个小时。乔木亭亭,鸟鸣嘤嘤。虽睹人迹,不闻人声。谷深流急,天若一窟。羊肠坎坷,水寒刺骨。师弟们不习山路,勉力而行。我说:“你们看,我长在这里,老天爷能让我进北大,我满足了,我谢天谢地。”
一生之中,有些事只有归之于天,才能表达出它对自己的深切意义。我曾是北大的学生,这是老天对我的眷顾。

(吾乡一巨石,浑浑当天立。生树树又花,疑是生花笔。右边是北大师弟,2016年夏到我老家一游。)